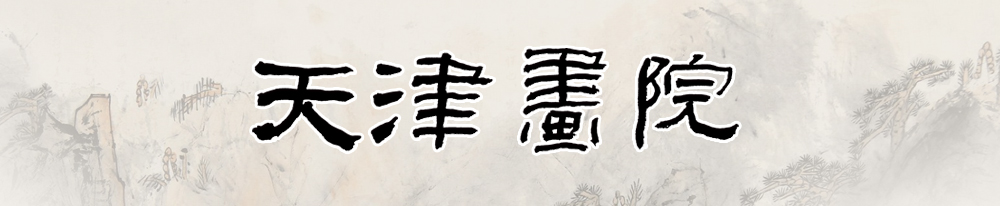尹沧海
学界对于京津画坛众说纷纭,就学理而言,京津画派并非是臻于完善的学术概念。俞剑华先生早在《现代中国画坛的状况》(1928年)一文中提出“京派”的概念,但其后这一名称并未得到推广。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画派画集》丛书,将“京津画派”单置一册,与海上画派、岭南画派并列,此举为推广京津画派这一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体而言,学界对于“京派”和“津派”绘画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从其内在线索、发展历程、代表人物与风格演进逐步展开。
(一)京津地域文化相异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西靠太行,北依燕山,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地。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北靠京城,东临渤海,古时既是军事要地,又是商贾云集的水岸码头;近现代以来,天津更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港则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和我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京津两市紧紧相连(距离120公里),交流便利,文化相融,形成了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经济文化圈。
战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一直处于中原文化和北方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边缘地带,它虽不是中原文化中心,却备受影响。换言之,北方各民族文化在此地交融,转向汉文化系统。中国画作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之下的子系统,随着时代的更替,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两宋,在北京这片土壤上渐次得以生长。而后,辽代以幽州作为陪都,北京的城市文化蓬勃发展;元后至明清,北京成为都城,强大的文化磁场吸引了各地画家赴京。当时院体画和文人画两大阵营繁兴,中国画逐步由边缘走向内核,北京画坛故而成为中国画在北方的战略要地。
天津成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城市是从明朝建卫开始。和古都北京相比,它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其绘画史同样年轻,据考,明末清初时才有天津籍画家被正式记载。天津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转折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英法由此取得长驻北京的权利,如同上海,天津也因此开埠并允许外国人居住。此后,清政府于1870年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撤销“三口通商大臣”(即北洋大臣),并由直隶总督兼任,李鸿章因此登上外交舞台,总督府也渐由保定转向天津(因此时“冬令封河,还驻保定”)。在其任职的二十余年里,创建北洋水师,发展扩建天津机器局,修建第一条铁路,开办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天津成了“洋务运动”的基地。袁世凯于1902年接任直隶总督,正式将总督署迁往天津,天津成为“北洋新政”的实验地。他建立近代警察制度,借助德国经验编练新军,发展新式教育和工商业。援引两个例子作为近代天津生态变迁的旁证:用20世纪初天津出版的《北洋画报》《醒俗画报》与同时期上海出版的《点石斎画报》《良友画报》作对比,均中西交融,新鲜奇异,但风格十分相似。“那时,上海与天津一南一北,同为东西文化相撞前沿的城市,社会形态差不多。从桌球(乒乓球)、玻璃丝袜(丝袜)到小洋楼,凡上海有的,天津也有。”①曹禺先生《日出》中茶房王福生和资本家潘月亭的生活原型就来自(天津)惠中饭店。“冯骥才先生则认为,《雷雨》和《日出》写的是那个时代地地道道的天津。”②资中筠先生成长在天津,他曾说:“1949年以前,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大城市。”天津地位的变化,正是经历了晚清的外交重心由“南重于北”转向“北重于南”而进入思想文化涡流的中心。
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美术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捩转,它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彻底改变密不可分。从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因北京是政治文化交战的咽喉,又一次吸引了大批政客和文人北上。当时,古物陈列所设立;北京一地有近八所美术专业院校开课,在天津有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美术副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于北京成立,并在天津设有分会,聚集了阵容强大的画家群体,尤以北京为主,京津画坛空前热闹。无论是深沉厚重的北京城,还是天津这一新兴城市,都在20世纪新旧思想的交锋中经受着时代的洗礼。正如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之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性格、地域特征、文化积淀、历史格局、审美意趣都会深深地影响艺术的走向
(二)应当肯定“津派绘画”独立存在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③鲁迅先生虽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文学之争,却为我们认识和讨论“京派”与“津派”提供了一种思路。
天津美术史学者崔锦曾著文《近代津门绘画杂谈》,王振德撰写《论津派绘画》,袁宝林先生则在2010年12月天津博物馆举办的“纪念刘奎龄诞辰125周年特展”学术研讨会上均主张“津派”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前文所述,天津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其特殊性,造就了别样的津门文化。但近现代以来,一方面,天津的区域地位较容易被上海等发达城市所压制;另一方面,京津地域相连,常被统称为北方文化或京津文化,因而天津独特的地位与价值多被忽视。所以,学界也有另一派观点称“津画不成派”或“京津不可分”。这一论断通常站在两派皆继承传统绘画的立场上,却不能整体囊括京派和津派不同的艺术倾向。
目前,学界对于“津派绘画”的部分论断与其对应的史实及画坛风貌不太对等,这一定程度上缘于20世纪中国画坛的矛盾与纠结。“津派”确是可以作为整体文化现象出现的。历史上,天津拥有不亚于北京的独特地位,有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中国的第一个现代美术馆——天津美术馆(始建于1930年,仿造日本东京上野美术馆所建)。天津拥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开放性,津派绘画也开放地继承中国绘画之传统,在吸收融合西方绘画传统的同时又巧妙避免了被同化,直接推动中国绘画的发展,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应引起学界重视。这种独特的艺术生态,不仅承载了艺术家的个体情绪,更承载着某种社会意义,不论过去或是未来,它始终会与时代紧密相连,成为反映社会精神氛围最为形象的脚注。
(三)“津派”与“京派”的联系与区别
在世界美术史范围内,画派的出现是寻常的美术现象,是推动美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画派的产生、形成和确立应具备三个重要条件:一为画家群体的出现;二是追求共同的艺术理想和主张;三是已经形成一个明确的艺术风格或趋向。而美术史对于画派的确立则建立在:一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记录;二是建立在对史实的认识基础之上。那么,以具有时代地域特色和审美倾向作为界定画派的理论依据,较仅仅以结社主张作为划分流派的标准,可能更具实质意义。
“京派”与“津派”是近代以来才被逐渐提及的范畴。辛亥革命后,国内政体发生改变,文化重心北移,文化价值形态随即发生变化。在官方扶持下,北京地区的绘画事业蓬勃发展,美术研究欣欣向荣。不同于沪上的结社方式,由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于1919年在北京发起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注重挖掘传统、研究国粹,反映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需求,具有起点高、视野广的特点,这一画家集群被称为“传统派”或“国粹派”。当时北京画坛新旧观念斗争异常激烈,矛盾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上。不少美术史家对京派的研究,只是界定在北京画坛“传统派”之上。袁宝林认为,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多元主张、多元艺术追求构成了对京派广义的解读;而狭义的京派则指“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一脉。20世纪,广义的京派呈现出三种格局:一是渐变传统之风,以金城与周肇祥领导的中国画学研究会集群影响甚大;二是传统文人画大变之风,以齐白石为代表,陈师曾尚处在大变与渐变之间;三是人物画之突变,以蒋兆和为代表,为徐悲鸿所支持。
北京是六朝古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而天津则为开放较早的沿海重镇,是文化和商业并荣的都会城市,二者所处的境遇不同。所以,当时北京画坛的传统派与融合派曾有激烈交锋,而天津画坛各类艺术主张相互影响的现象较为明显。从师承渊源和画家构成两方面梳理天津画坛,除少数个案外,主要有四种趋向:其一是延续本土文化传统;其二是海派艺术的影响:其三是租界文化影响下的中西合璧;其四是“京派”艺术的异地传播。值得提及的是,天津画坛职业画家为多,他们较少有江南文人的执拗,但凡西方绘画的可鉴之处,都能给予他们新鲜的感受和刺激,他们不断尝试,体味中西融合给传统绘画带来的微妙差异。晚清以来,文人画在天津并不占主流,水墨写意一门也较为冷清,而天津画家在花卉一科中展现出的对西洋画法的兴趣,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画家在创作中为营造鲜明的色彩效果,将普鲁士蓝、西洋红、胡绿等西方颜料引入中国画创作中,其突出特点是打破了传统文人画的雅俗鉴赏观。刘奎龄是融贯中西的代表,他没有留过洋,也没有接受过学院派的教育,但他在中西文化互渗的天津寻找到独有的绘画语言。但是,在刘奎龄生前,他的作品都没有受到国内画坛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其画名、画价才陡然升温。由刘奎龄的现象得知,在“中体西用”的探索上,天津画家与北京画家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艺术实践,其代表画家还有张兆祥、陆辛农、李老同等人。
(四)“京津画派”指称的开放性
200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京津画派》一书,作者为何延喆。此书中界定的“京津画派”,地域范围是比邻接壤的京津两地,时间约为整个20世纪,画家与流派既涵盖引西润中求改革的“融合派”,也包括借古开今的“传统派”。他强调20世纪京津画坛的多元与丰富,如此包容不无道理。此前,在从事美术研究、收藏与流通的从业者中,京津画派这一称谓已常用,然而其指涉的画家与流派,大多仅是传统派这一小范围,较少涵括融合派。
“京津画派”的艺术风格难以一言以蔽之,它复杂、丰满又极具时代气息,它既包含金城等人所倡导的“精研古法”,又有陈师曾大变有成的“文人画”之风貌,有徐悲鸿极力推行的“西化”美术教育模式,有津门各家“西学为用”的高度融合,更有特殊时期的“红色经典”等等。无论何种画风,皆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近年来,“京津画派”逐渐从约定走向俗成,如“海派”一般,是该地区众多画派及个人艺术风格的集成。“流派与地域画风多元共生,表明中国当代美术已走出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化场域,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自叙和自设成为中国现代美术追求现代化的目标。”④京津画家群体将在鲜活的世俗生活中,以其开放的、包容的、传统的、民俗的特质,以敏锐的民族主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吸收整合西方绘画视觉因素的优长,不断创作出广泛受众喜闻乐见的绘画作品,无论现在或是将来,它都会在民族艺术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节选自尹沧海《天津书画艺术史》2017年
[1]冯骥才:《醒俗画报》,中国作家网,2007年3月19日。
[2]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3]鲁迅:《“京派”与“海派”》,原载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转引自《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2页。
[4]姜寿田:《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1985—2005》,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