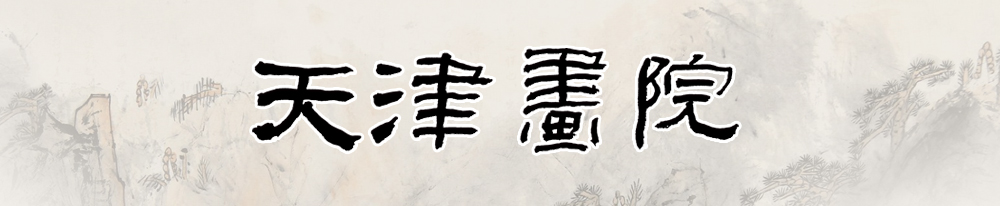薛永年
在我心目中,京津画派的名称出现较晚。去年十月,首次出版《京津画派》,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列为“中国画派丛书”之一,作者是我的同行朋友何延喆。何延喆界定的京津画派,地域是接壤比邻的京津两地,时间大略囊括整个20世纪,画家与流派既涵盖了引西润中改革中国画的融合派,也包括了借古开今吸收新机的传统派。他强调的是20世纪京津画坛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如此包容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在此之前,在部分从事美术研究、美术收藏与美术流通的人们当中,已经有了京津画派的称谓,然而所指涉的京津画家与流派,大略仅仅以传统派为范围,不涵括融合派。
这也并不奇怪,原因是京津画派名称的提出,比京派绘画为晚。记得在21世纪之初,我和一些美术史界的朋友发现,在论及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画坛时,很多著作和文章还沿袭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认识,除去孤立地称道齐白石以外,总认为北京是最封建、最顽固的堡垒,是守旧、保守势力的重镇。然而, 自湖南移居北京的齐白石,不仅恰恰在北京完成了衰年变法,而且与很多北京传统派画家是好友,他之脱颖而出又在参加传统派团体的日中联展之时。郎绍君弟子对金北楼等个案研究表明,以顽固守旧的说法来评价齐白石以外的彼时北京画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一个亟待重新研究的问题。
为此,我在2001年发表了《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之后,便与北京美协理委会的刘曦林副主任、单国强副主任、陈履生秘书长,一道向北京市文联申报了京派绘画研究的课题,同时以各种形式提倡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京派绘画。虽然我们申报的课题并没有引起审批部门的应有重视,但在郎绍君先生与我们不谋而合的努力下,一些国内外和两岸学者纷纷从个案开始做起京派画家来,其中尤以金城、陈半丁、徐燕荪和陈少梅等家的研究、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两个社团的研究收获最大,钩隐抉微,突破成见,恢复了被一度遮蔽的历史面目。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京派,由于结成了超越地域的绘画社团,影响亦波及各地,津京近在咫尺,北京的湖社画会即在天津设有分会,所以津门的传统派实为京派的流脉。当然,京津毕竟一为传统文化丰厚的故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一为开放较早的沿海重镇和文化与商业并荣的都会。两者所处地位的不同,导致北京画坛传统派与融合派曾有过激烈的冲突,天津各派的杂处与兼容更明显一些。不过,若从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派而言,只涉及反映京派流风余韵的那一部分天津画家,也就顺理成章了。据说以研究陈半丁知名的年轻学者朱京生所申报并被获准的京津画派研究课题,对京津画派的界定大体也持这种意见。
假如按这种对京津画派的界定,那么该派的画家基本列籍于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分析这两个本质上以“精求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的国画团体中的著名画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们并非都是北京人,相当一些名家来自受到海派大小写意影响的南方,在艺术中感染了市民气息。二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井底之蛙,相反却有着留学外国的经历,甚至对西方的古今绘画有着较多地了解。三是他们精研的传统,已不限于晚明董其昌以来的正统派传统,对于两宋传统(包括所谓北宗传统)、对于以石涛等家为代表的明清个性派传统、对于以郎世宁为先行的中西合璧传统,都有所取法。
其实,京津画派的传统派画家与融合派画家在文化价值观上,都是坚持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所不同者仅仅在于融合派的艺术更多着眼于艺术的经世致用和艺术语言的视觉观念之变,而传统派画家却坚守着艺术语言的民族性与继承性,坚持着艺术作为赏心乐事的娱情性,不大乐于接受西方的视觉观念。传统派画家也并非一味临摹,而是和融合派画家一样地重视写生、重视师造化,但主张“以古法写生”,以便继承发展传统的艺术语言。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京津绘画的发展,是在融合中西的改革派与借古开今的传统派的互动与互补中实现的,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站在改革派立场发表的极端看法。
一般而言,京津画派成员的范围,大体包括在京津两地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的会员之中,满族画家组织松风画会的会员也在其内。他们虽然富于传统文化修养,诗书画兼擅,但已属主要靠卖画及在美专教学为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中的名家主要有金城、陈师曾、姚华、周养庵、萧谦中、萧俊贤、贺履之、余绍宋、徐宗浩、汤涤、金陶陶、溥心畬、溥雪斋、陈半丁、胡佩衡、管平湖、俞明、徐燕荪、马晋、刘凌沧、吴光宇、吴镜汀、秦仲文、惠孝同、赵梦朱、王云、于非闇、王雪涛、汪慎生、祁井西、田世光、陈少梅、刘子久、张其翼、颜伯龙、李鹤筹等,齐白石的弟子李苦禅、许麟庐等亦应列入,但在已出版的美术史中,上述画家大多付之如。
如今,随着经济腾飞,人们多方面审美需要诉求的增长,收藏鉴赏风气大盛。收藏家与从事艺术品经营的人们,已无法满足于只关心过去绘画简史上列名的少数画家,而是实事求是地开拓疆土,发掘宝藏。所以,总起来看,学界对历史遮蔽的京派画家的研究,尽管意识较早,却远远赶不上市场从业者的多知与勇敢。举例来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常在画友张兆基的家中看到王心竟的山水,记得这位画家钟意北宗,画风有些接近陈少梅,但对其人一无所知,也未曾听到美术史家提及,直到近年他的作品不断在拍卖会上出现,才知道他也是金北楼的弟子。这样看来,按治学的规律和市场运行的规律,京津画派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深入研究成果问世,而且其市场的势头是会越来越好的。
2006年7月
原载于《中国书画》2006年第六期
*选自薛永年著《方壶楼画引》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