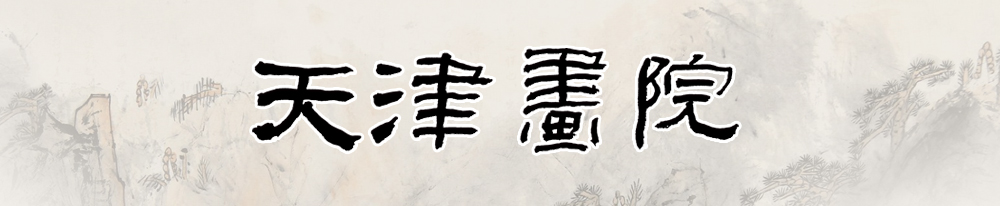——读霍春阳先生观窑瓷绘新作
孙飞
沽上的观窑主人赵总将恩师霍春阳先生(行文不避名讳)的瓷绘近作发图与我,邀为作评。鉴赏之余欣欣然,而后诚惶诚恐,谨记所思如左。
中国无疑是一个“瓷器之国”。考古者常说:陶器为人类所共有,瓷器乃中国所独创。瓷器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技术与艺术上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随着考古的近期发现可以证实,中国最迟在周时便已出现原始青瓷的烧制。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大多能够掌握制陶技术,而只有中华文明通过提高窑温,调配釉料,创造了这交融着水、火、土的艺术。然而概览中国陶瓷史,宋代以前有所谓“南青北白”之说,一青一白两大瓷窑系统并驾齐驱,青似千峰翠色,白则类雪若银。或似明月染春水,或如玉盘承凝露,圆如桂魂坠,轻似云魄起,水归器内在人世间呈现出各自的青白与方圆。从中国陶瓷发展史看,在青白两大瓷窑系统之外,釉下彩绘的装饰手法早在唐代长沙窑,便广泛地得到发扬。那些花草与雀鸟,气韵生动,一派天机,显示出长沙窑工对造化的体察入微与绘法的娴熟。尤其是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那是原版的唐代社会风情的吟唱,或抒离情别绪,或叹世态炎凉,或写商贾宴乐,或描边塞征愁,今校之以《全唐诗》,其间亦不乏骚客辞卿之作。苏东坡曾谓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或许正是中国文人画风气滥觞于唐的民间物质呈现。虽然以往的诸多学者,多据年代早晚,并无证据地认为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装饰技艺,影响了后世磁州窑的“白地黑绘”装饰。但从现存作品看,这种参与工艺制作的“文人墨戏”风气却是可能的。宋代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于世,上自皇室公卿、达官显宦,下至幕僚胥吏、乡绅士庶,构成了一个比唐代远为浓郁的文化氛围。诗文书画在不同的阶层得到普及,而作为“载道之器”更能以一种不言而喻、润物无声的方式滋育慰藉着世道人心。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宋代文人画的诗情,书法的意兴,相比宫廷绘画的工致谨严,或许更能切合于民风日用,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在宋、金、元的战乱中,多少落难士子的愁怀,隐逸文人的悲肠,都付于那晶温莹润、冰清玉爽的一枕词令,梦里沉吟,枕边看花。他们达则济天下,穷则善其身,在穷达之间道器不离,以一种可官可民的姿态,一以贯之得续写着文化道统与学统。随着战乱中北方工匠的南迁以及元代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陶瓷的彩绘仿佛寻到一张白洁莹润的宣纸。而元代至正间引进的苏麻尼青(近年亦有他说,本文不作赘述),高温下譬如徽墨的五色晕染,恰似一场历史的际会,开启了元明以降瓷器的青花与彩绘时代。然而,随着景德镇陶瓷彩绘的日趋宫廷化与世俗化,难以复见昔日长沙、磁州诸窑那般鲜活的生气,或许也可无奈地从中读到一丝文明后期的封闭与衰落。虽然近世亦有“珠山八友”之称,以笔者的浅见,“御窑厂”流落于民间的技艺,譬如裹足后的放脚,早已难成天真。如果说瓷器的彩绘是一种艺术,那么所难得的正是运于灵府的性情汇与祝融之火中难测的天成,又岂但以“工艺”而论焉?所幸者是这个开放的时代,艺术家们又一次广泛的参与了工艺,一时间瓷器的彩绘仿佛成为了当代书画家的一种风气。期间或许良莠芜杂,又或许成败相间,但窑火的噼噼啪啪中奏响得也许是一种天籁,窑神或亦曰:“你道我一生爱好是天然”。
瓷器毕竟只是一种器的存在。孔夫子说:“君子不器”。君子心怀天下,不能像器物一样限于用的方面。《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当然是志于道的,《中庸》有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器者,物也,形也,当然不单是器皿,所有有形的物质存在都是器;而大道无形,是所有器物所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总的法则。有形即有度,有度必满盈。是故,君子之思不器,君子之行不器,君子之量不器。恩师霍春阳先生,当代书画巨擘,一朝圣手。然则在其几十年的从艺生涯中,从来未满足囿于一技之长。其深谙中国书画的法式语言同中华文化学理的表里关系,梦读诗书,善省经典,用自己的人生沉浮深刻体验着“八卦震荡、刚柔相济”的乾坤大道。从此种意义审视老师的艺术生涯,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老师恐怕不是“个中人”,老师分明是一“道中人”。说实在话,在他成长经历的时代中,不随波逐流地应对现实,不人云亦云地独立思想无疑是困难的。尤其是“以法入道”的路与“由象臻理”的要求,更是难上加难。老师并没有在通常的辞章歌赋中寻求所谓的画外功夫,他选取从哲玄思想的源头去参照自己的艺术与人生。静观外物,默省自身,从而迎得一种闲和严静的清明。老师常对我言:“知道者易,行道者难” ,他的这种实践躬行之学进而养成其基本人生态度与精神情愫,兴物托象,濡笔噬墨,修成文化对艺术与人生的造就。逝者如斯夫,余以不雕之才,有漏根因,从师游匆匆廿又六载,师又早逾古稀,或谓人书俱老,名心退尽道心生矣。曩者,尝读阳明先生论致良知,谓:持经达变,抱一应万,待人接物事事可为,今睹师之行状或已然入此境乎?然而,老师道心即明,却转而为器,近来颇作瓷绘。王夫之也曾说过:“道不离器”,提出过“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认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周易外传》)。大概而言,没有事物便没有事物的规律,只能说规律是事物的规律,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历史的看,这当然是对宋明理学虚浮空泛的修正。船山先生的学说,多继承张横渠。笔者当年曾得老师所藏《张子正蒙注》,翻阅数通,直至今日方可略知其味,而“道器不离”的宗法或许老师早已谙熟。原来无论为学,无论为艺,不过是为人,寻一条君子的修成之道而已。器与不器都是君子,论器即是论道。
其实老师画器从未间断。2004年,陈绶祥老师(此亦不避名讳)便组织策划了一套《大器丛书》,其中便有老师作品一卷。糯米般的高岭土白胎,透明釉,或青花,或釉里红,器型舒展有致,发色浓淡相宜。尤其是那釉里红的鱼儿,虚静空灵,如缥似影,宛若青白的天际呆住了一朵彤云。今复见老师的观窑近作,亦非争奇斗艳,依旧疏淡玄远。题材是一如过往的文人所衷,唯那牡丹与新荷的红,在如烟的青色中见出些许冷艳,譬如碧竹间、暮烟中冷羞的茜袖。而大面积的留白,晶莹通透,那是天空,是虚无,是周流于天地间惟恍惟惚的气。而那器上的所题,偏又多语出经典,全然是器以载道的琳琅。老师乘于物而游于心,怡然自得,何其逍遥快哉。
唐代李德裕喜欢藏石,传其每获奇石,皆予品题,并于石上镌刻“有道”两字。今观老师观窑新作,取陶诗“欲辨已忘言”的此中真意,欲为之名“有道”系列,未知老师以为然否?
壬寅孟春于懒云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