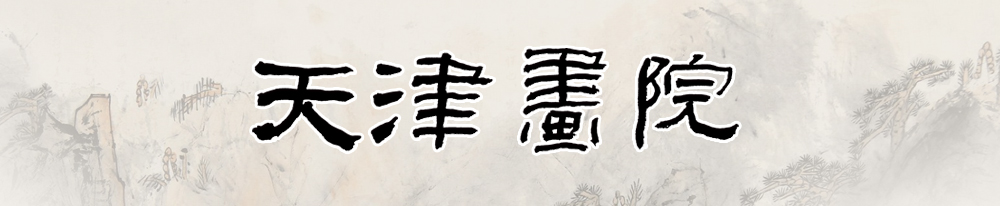——《零点》和《儿女情长》
陈治、武欣
叙事性的绘画不论中西,都是一直以来存在的,中国传统绘画里的《宫乐图》《洛神赋图》《捣练图》,还有《女史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都是叙事性绘画。在历史的当时,这类绘画的功能性占着主要地位。或“成教化,助人伦”,或记录当时的时代风貌、人物事迹。流传至今,审美性的强化伴随功能性的减退,或者这两者皆存在。当代绘画,尤其是现实主义绘画,不可否认就是功能性和审美性兼具的。现实主义绘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有良好社会效用的、反映时代风貌的绘画。为社会的正能量发声,为普通人服务的艺术思想是中国现实主义绘画的根基。我们的绘画是当代现实主义绘画的一部分。
2009年我们创作的《零点》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银奖,2014年创作的《儿女情长》获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金奖。这两幅作品都基于对这个时代的关照,情感出发点来源于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人,都描绘了家庭题材。一个表现了年轻人在新的家庭成长时所面临的无奈和希冀。另一个则是对家庭的温情和眷恋。这两幅作品都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展现的是世间最温情的画面。当人们从画面中寻得最为熟悉的情境时,当人们从画面中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影子时,必定心生暖意,感动油然而生。这种感动来源于画家的真挚情感,来源于对生活真切的表达。古人说“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最根本所在,也是绘画的真谛—本乎真情,发自真心。我们始终觉得画自己有所感悟的生活,才是最符合自我的表达方式。这正是“以心造境,以手运心”的初衷。
《零点》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处于新阶段的80后小家庭的生活现状。现代人繁忙、紧张、拥挤、疲惫、惶恐的精神世界,在这张画里显现无遗。疲惫的神情,微妙的疏离,也让人感到了现代人的无奈,“爸爸”似是无聊又似是专注,“妈妈”情绪不高,微微扭动的身体流露出慵懒,连衬衣和睡衣上凌乱的衣纹似乎也在诉说纷杂的情绪。而《儿女情长》展现的是在外地工作的儿女回家探望父母的温情画面。叙的是回家的事,抒的是父母儿女的情。相对于《零点》来说,情感的表达更为深沉,画面更加复杂。虽然仍在表现家庭,却已经将视角放到更广阔的层面上来,从小家庭的起步转至大家庭的喜乐悲欢,表现真实而生动的回家探亲的场面,亲情在画面中每个人的情绪中流淌,热烈而又伤感。
这两幅作品表现的都是“情”一字。夫妻、父母、儿女之间都是亲情,在柔肠百转间,不圆满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石涛说“参差历落,一味不尽人情,偏能令情深者徘徊而不能去”,正是画面里表现出的那一丝“不尽人情”却是最能令人动情之处。《零点》隐约的疏离,《儿女情长》看似圆满却暗示的分离,都是人生的遗憾和无奈。以情动人,以情化境,“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恽格)。为家庭和生活的沉重而落寞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展示礼物的孩子,追随着亲人身影的目光,每一个点都既是物也是情亦是境。在《零点》和《儿女情长》中,我们没有像以往的作品那样以中国艺术传统的处理空间的多点透视,计白当黑的方式,而是将画面画的很满,东西画的很多,除了画面的主要因素-人物,更刻画了很多多余因素-物品。细节的铺陈在这两幅作品中占了相当的分量。这些小细节也都是为突出“情”而安排的。
《零点》中略带孩子气的小玩意就是还没真正成熟的年轻父母心态的代表:玩具熊、卡通相架、小象咖啡杯、黄色的小闹钟、小瓷狗,都在表示,虽已经为人父母了,自己还没有成熟却要承担生活的责任。在这幅画里还有一个一直未出现的人物——孩子,但观者却能从细节中感受到这个家庭里孩子的存在:茶几上的串珠玩具、妈妈手上的奶瓶、小桌下藏起来的电动火车、卡通相架里孩子的照片。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节就能拼凑出一个小家庭的生活场景。小甜蜜和现实的无奈碰撞出生活的感悟,温馨的家庭也会有个体的失落,这或许也是生活的真谛。
《儿女情长》中的“小道具”的作用发挥的更加突出。最能点出“回家”这个主题的就是面条,中国北方有这样的习俗,亲人从远方回家来,第一餐要吃面条,寓意长接不走,留在家的时间长长久久。这样的民俗,这样的面条,妈妈扬起的双手上没来的及洗去的面粉和身上穿着的围裙都是围绕着孩子回家探亲这个主题的。我们也赋予了皮箱的新的意义,旅行箱打开,是到家团聚的开始;当皮箱合上,就是又要出发的时候。这次的团聚也预示着下一次的分离。桌子上的水果、给父亲带来的药盒营养品、小孙女的草帽和书包、日历上标注着“到家”的日期,这些也都是围绕在回家探望父母的主题上。亲人之间的情谊和伤感的情绪在细细体味之时明确出来。每个物品都是推动剧情的道具。
工笔画是一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很适合表现叙事性的绘画。它可以展现古代人的宽袍大袖,繁复的衣纹褶皱,也可以表现现代人的衬衣、牛仔。它可以相当完美的表现出所绘之人之物的情状,可以说工笔画的美感也恰恰就在画面展现的工净匀停,韵致安然,细腻写真之美。工笔画最令人诟病它的就是“工细”。然而,“极工而后能写意”。“写意”才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真正内涵。是超越形象物态之外的内在气韵和意境,是画家思想情感的延伸和寄托。是什么样的形制不是关键,不管工笔还是写意,写实还是变形, 都以“意”是否得到了彰显,超乎物外的精神是否得到了体现而论。叙事性绘画的主题是人物,这两幅作品每一个人物的造型都是最符合主题符合情感走向的,主次人物之间的安排相互呼应有序,使得画面法度得宜。对形象的选取既注意了没有过分美化,又兼具了形象的特征和情绪。丝丝缕缕的情感就在人物的眼波流转间蔓延。如果说叙事性绘画仅仅是叙事,那就太流于表面化和故事性了。叙事要有故事,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画面讲故事的同时传达出人物的情感,这情感里既有所绘之人的愿望,也有作画者的理想。
这幅作品的画面里,什么是最具魅力的审美因素?在我们看来那就是线。重视线的表现力,线的韵律感、书写感。线就是支撑起整篇文章的优美的字词,又像是流淌的音符,旋律低回,意蕴悠长。中国画的线就如骨架,将一幅画支撑起来。我们始终力求将线运用的既状物又抒情,既工整又写意,既具象又抽象。现在对工笔画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也确有不良之作乱世人之目。所以,画出纯正的、有格调的、有生命力的工笔画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
古人说“五色乱目”,并不是说不能用色,而是说要节制用色。谢赫六法之一便是“随类赋彩”,这里的“随类”其实颇富思量。艺术化的处理,用色的主观性,色彩的协调性都在其中。在《零点》和《儿女情长》中色彩也是具特色的,而有异同。两幅画都运用了无色系(黑白灰)和补色来呼应中和,都用了暖色调。但《零点》表现的是年轻人的家庭,色彩必然明快清新。《儿女情长》表现的是老年人的家庭,色彩应该沉稳和谐。画面的色调温暖柔和,暖色调的赭、褐、黄、绿的协和搭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色彩观既继承了传统的观念,又遵循了科学的用色法则;既有对现实的参考,又有对色彩主观的处理。工笔画的时代性也需通过色彩来体现,每个时代的审美习惯都不同,对待传统要继承也要发扬,既要遵循规律又要创新想象。而用色的宗旨就是要“雅健、清逸”(王昱)。色彩的格调是决定工笔画格调的最重要因素,赋彩的格调从立意中来,从单纯中来,从和谐中来,从简洁中来,从沉静中来。
叙事性绘画不是只叙事只做文学性的描述,而不重情不抒情,其恰恰是借叙事来抒情,叙事性抒情,在人们阅读绘画的同时,和作者,情感与共,审美与共,思索与共。
*本文发表于2018年8月刊《美术观察》
|